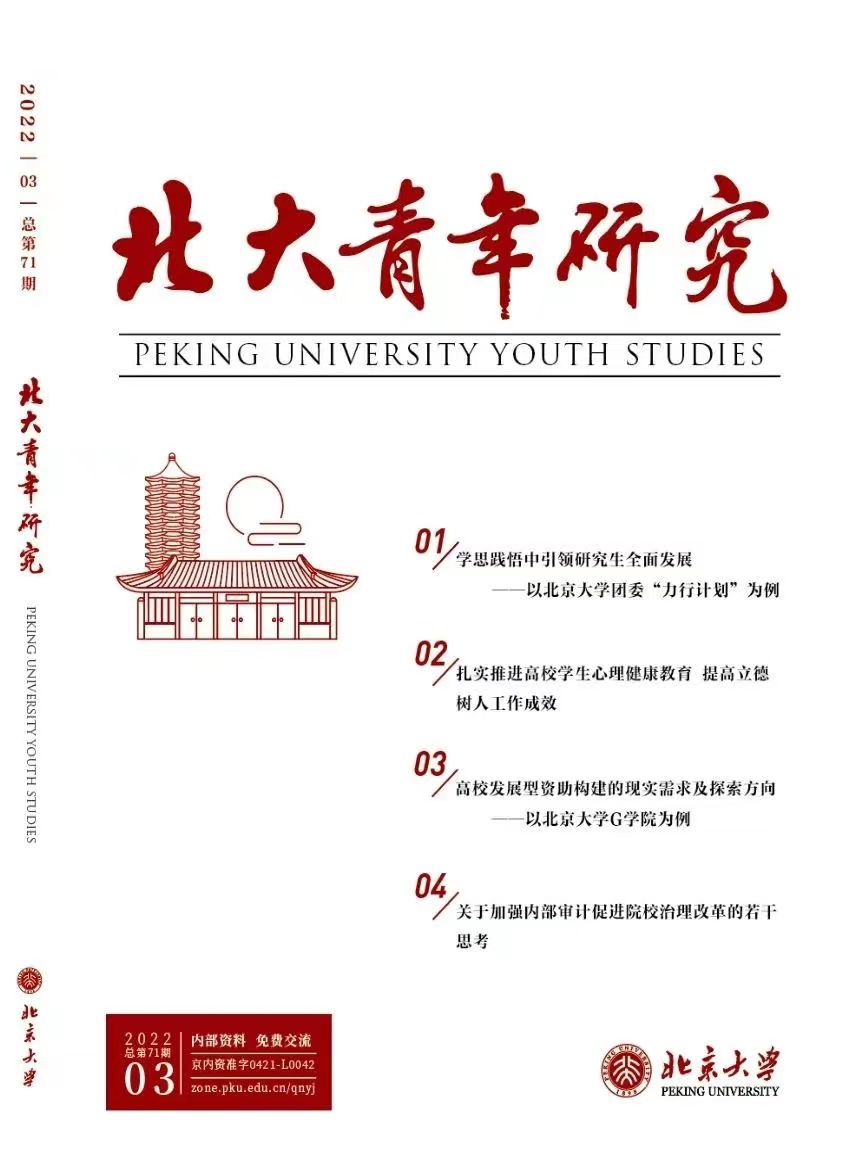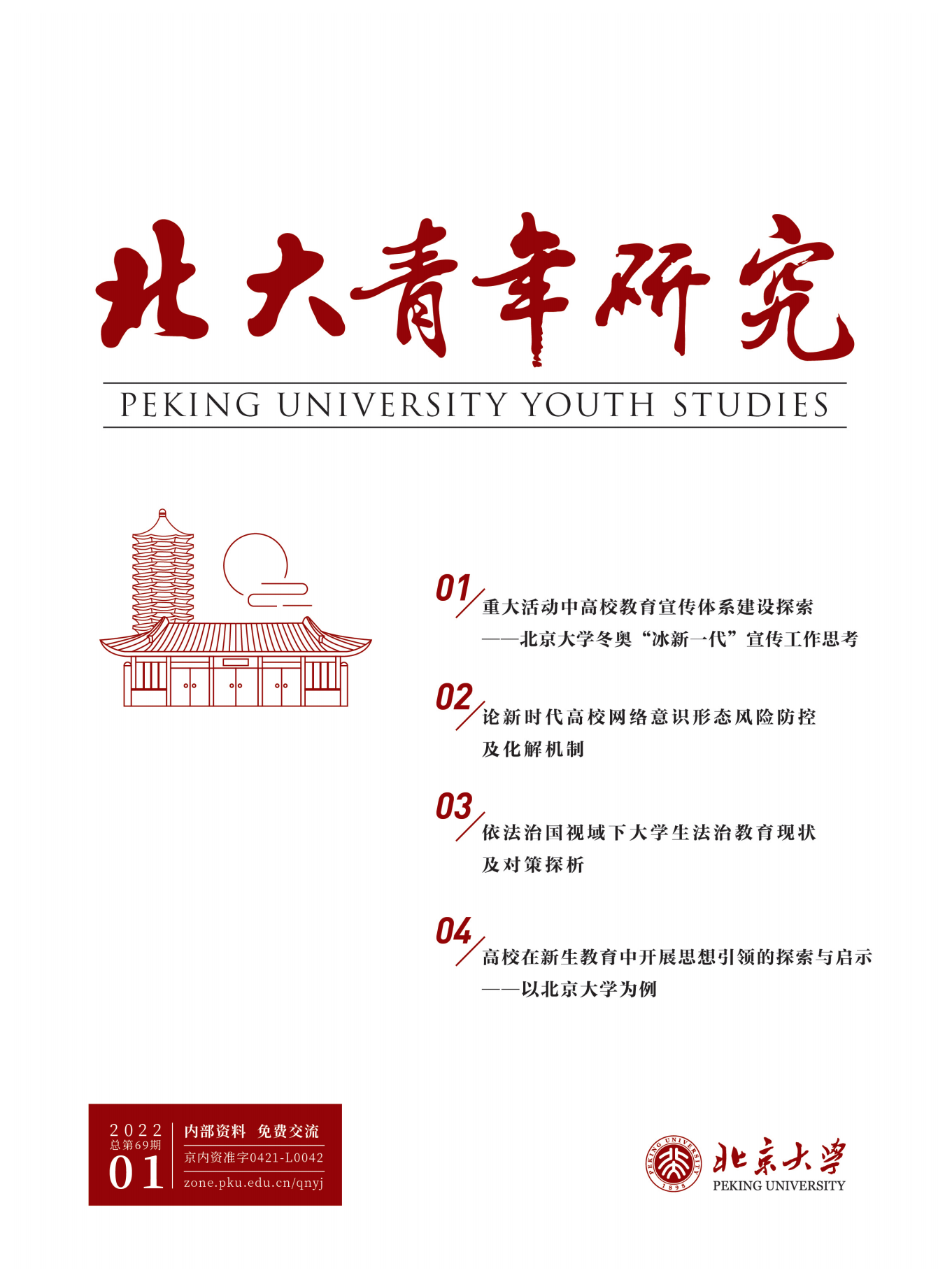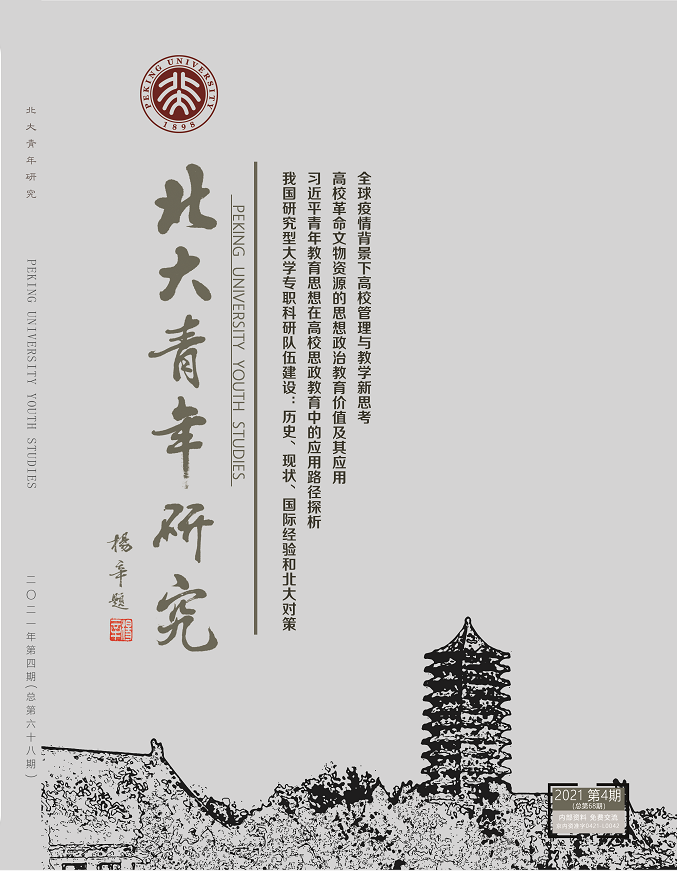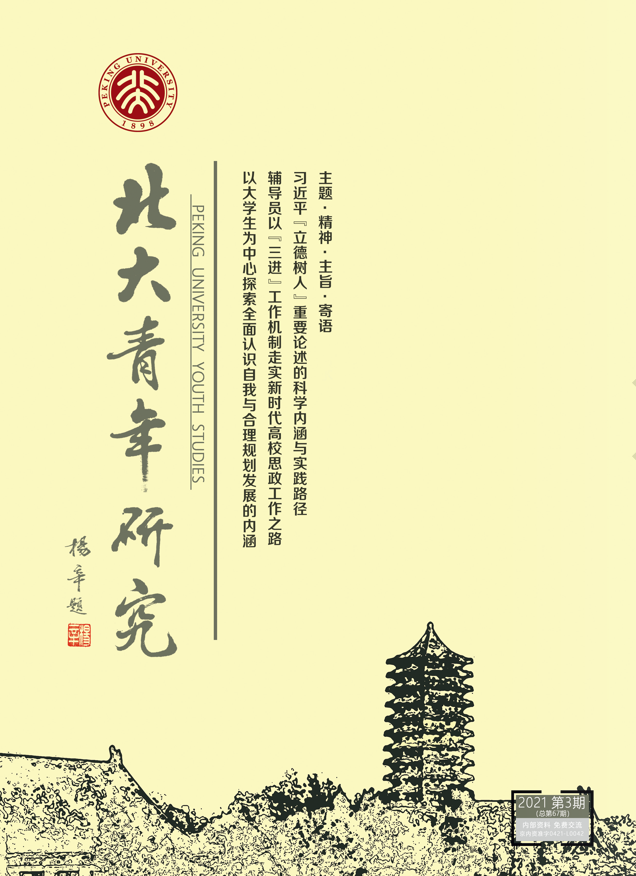编委会
封面题字: 杨 辛
主办单位:北京大学
顾 问:王义遒 林钧敬 张 彦
编委会主任:陈宝剑
副主任:陈占安 徐善东 王逸鸣
户国栋
委 员(以姓氏笔画为序):
王天兵 王艳超 冯支越 匡国鑫
孙 华 关海庭 陈建龙 刘 卉
刘海骅 宇文利 吴艳红 李 杨
陈征微 金顶兵 查 晶 祖嘉合
夏学銮 蒋广学 霍晓丹 魏中鹏
刘书林(《思想理论教育导刊》常务副主编)
杨守建(《中国青年研究》副主编)
彭庆红(《思想教育研究》常务副主编)
谢成宇(《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》社长)
屈晓婷(《北京教育(德育)》副主编)
夏晓虹(《高校辅导员》常务副主编)
周文辉(《学位与研究生教育》社长)
李艺英(《北京教育(高教)》社长)
郑 端(《思想理论教育导刊》编辑部主任)
陈九如(《高校辅导员学刊》副主编)
毛殊凡(《中国高校社会科学》总编室主任)
主 编:王艳超
编 辑:许 凝 马丽晨 朱俊炜
王 剑 吕 媛 李婷婷
李 涛 侯欣迪 杨晓征
宋 鑫 张会峰 陈秋媛
马 博 陈珺茗 陈 卓
审 校:青年理论办公室
从历史中走来的北大政治理论课(1949—1992) ——四位老燕大人的口述史整理
人物简介:
冯瑞芳:1928年4月—2021年7月,广东顺德人,1948年9月入读燕京大学教育系,1952年9月到北大中国革命史教研室工作。
王隽彦:1928年7月,山东人,1947年9月入读燕京大学经济系,1951年9月燕京大学毕业留校,1952年转入北大经济系工作。
姚曼华:1928年11月,浙江吴兴人,1949年9月入读燕京大学哲学系,1952年9月毕业到唐山交大,1957年4月调入北大工作。
李庆聪:1930年7月,沈阳人,1949年入读燕京大学教育系,1951年提前毕业,留燕京大学任政治课辅导教师,1952年转入北大中国革命史教研室工作。
一、从燕大到北大
几位老师是哪一年来北大的,请问那时的政治理论课是什么情况?
冯瑞芳:王老师是1951年燕大毕业,1952年转入北大,她是经济系的。李庆聪是1951年燕大提前毕业,1952年转入北大。我是1952年毕业,毕业时刚好院系调整,我就分配到北大,所以我们讲,只能讲1952年以后的一些情况。据我了解,1952年那时候在北大,设有四门的政治理论课,一个是中国革命史,一个是马列主义基础,一个政治经济学,一个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。当时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是由系里头负责的,没有单独成立一个公共教研室,中国革命史是独立的,我跟李庆聪两个是在中国革命史教研室,我毕业以后就从事这方面工作。另外当时还有一个马列主义教研室,当时还有十几个人吧,目前还在北大的没几个了。
李庆聪:解放后,为了加强政治思想教育,教育部通知各高校建立讲授公共政治课的组织。燕京大学党总支委员会决定抽调燕大的党总支委员、分管宣传工作的张世龙同志担任主讲教员并筹组教学班子。为此从化学系、社会学系及教育系各抽调一名学生团员担任辅导工作,我是其中之一。当时政治课是在办公楼礼堂上大课,上学期讲“社会发展史”,下学期讲“中国革命史”,教材有艾思奇的《社会发展史讲义》、胡乔木同志的《中国共产党三十年》、华岗的《中华民族解放史》等。1952年高等学校教育改革,几所高等院校合并调整,成立了“新北大”。十月份,教育部发出《关于全国高等学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课程的指示》,根据这个通知规定,从1952年起学校开设了相关的政治理论课程。为了加强“中国革命史”课程小组的领导力量,当时从文化部办公厅抽调了一名老同志——张凌青担任主任,副主任为原北大学生会主席、党委委员许世华同志。此外还有岳麟章、张俊彦、陈哲夫、田昌五等十多人。其中萧超然同志1951年被派到人民大学进修“中国革命史”。在教学中为了提高教学质量,抽调业务较强的同志统一编写讲稿;较弱的成立互助小组,分析学生思想动态、研究讲稿、观摩教学,就这样,教师队伍壮大了,领导力量加强了,一切走上正轨。
姚曼华:我是燕大1952年毕业的,当时已经是三校合并,就是辅仁、燕大、北大的文科合并。快毕业的时候,当时在哲学系,没有考虑直接留在北大,后来我就分配到唐山交大,现在叫西南交通大学,在成都。唐山交大让我们教党史课,其实我们学的是哲学,都是赶鸭子上架。到了那里教党史课,后来就送到人大进修两年,1953年到1955年,回校以后就开课,按照在人大学的老师给的讲稿,就按照这个讲稿讲就行了,再后来,1957年我来的北大。
二、去党校、人大进修
几位老师是哪一年去党校、人大进修的,请问当时情形如何?
姚曼华:我是燕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的,但毕业的时候我们这些入党的积极分子就都被分配到教党史课去了。我们一点基础都没有,真的,1953年就去人大进修了两年,听何干之他们讲,把他们的讲稿拿回去,后头再自己慢慢地一点点地研究。那时候全国的大学大概都是何干之的讲稿。人大办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班,两年,出来呢就是研究班毕业了,然后回家呢就讲课。我们都是带着工资去的,学校送去的。基本上全国各地大学的思政课教员都是送到人大去学习。我在唐山交大嘛,我是第一个派出来进修的,第二年又派一个,第三年又派一个,所以我们当时讲的政治课都是人大的版本。
冯瑞芳:当时学校党委有一个决定,就选派一些青年教师到党校和人大去学习。我是1954年2月份去的党校,当时不叫党校,叫中央马列学院,后来改成中央党校。当时学校党委派了我和龚理嘉去中央马列学院,龚理嘉是经济系的。因为我是从中国革命史教研室去的,所以就去学中国革命史。当时马列学院有一个单位,叫师资训练部,就是从全国各个高校选派青年教师去培训,我跟龚理嘉两个人就参加师资训练部。我们当时算年纪比较轻的,还有一些年纪大的,30、40岁就是老革命了。到那里去本来是要我学中国革命史,学党史的,当时党委考虑到哲学青年教师少,要我改学哲学,所以我是去了那里才学的哲学。当时师资训练部有党史,有哲学,有政治经济学,几门政治课都有,我就根据党委要求参加了哲学支部。当时有苏联专家讲课,按照苏联那套体系,讲辩证唯物主义、历史唯物主义。另外还有国内一些专家如艾思奇、胡绳和孙定国这些老的理论家也来讲课。我们在那儿待了两年,1956年2月毕业了,我就到了哲学系。我们那批去了以后,后来张俊彦也去了,他是五班,我是三班,他比我晚两年。因为当时党史有专门的教研室,马列主义基础有专门教研室,哲学和政治经济分的系,所以我从党校回来分到哲学系,然后给经济系和历史系的学生讲哲学。
李庆聪:为了提高教学质量,首先需要认真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。我们轮流被送到中央党校和人民大学进行培训。我是1955年至1957年在人大马列主义基础研究班进修的,同去的还有季国平、黄美复等人。崔懿华同志比我们早就去人大进修了。毕业后返校,时值1957年反右高潮,又有1957年12月高教部的通知,各校暂停四门政治课教学,一律下放基层,参加生产劳动。我们北大下放到门头沟革命老区斋堂及清水等镇,一年后返校恢复教研室活动。
三、政治理论课的教学
建国后北大政治理论课也经历了很多变化,请问当时教学是什么情况?
冯瑞芳:当时中国革命史教研室有一位老师专门负责写讲稿,叫张俊彦,现在人已经不在了。所以当时就由他负责统一的讲稿,另外老师就以他的讲稿为基础,再补充一些材料自己发挥,当时是这样讲课。所谓中国革命史实际上讲的是党史,按照党的不同历史时期这样来讲,土地革命时期,抗日战争,解放战争这么来讲。我从党校回来,就在历史系和经济系讲,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,就是苏联专家讲得那套东西。后来到1958年左右,学校又有一个措施抽调一批高年级学生出来当老师。那时人手不够,哲学系有本系的课,还要面对全校。从60年代我就没讲大课,我就给哲学系里头讲基础课,给一二年级讲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。后来马列教研室又经历了很多分分合合,到1988年学院成立前我就退休了。
王隽彦:我在北大工作37年吧,20多年是属于经济系的,回到马列主义教研室是1978到1988,然后退休,就十年。我可能记得不准,反正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在经济系的时候,就有对全校政治课的这样一个组,叫外系组,就是给别的系讲课的,有十几个人,这是马列主义教研室以前在经济系的情况。我在外系组待过,也教过本系的,本系主要是在1957、1958一直到1962年。这个外系组在文化大革命刚刚过,那是六几年吧,可能是1971、1972年,这个组很兴旺,在经济系什么大人物都来了,一个是蔡次明,蔡次明都在我那儿当过教员,蔡次明跟我是燕京同班的,他在区县当过头儿,后来还是回教育部了。我的记忆力不好,说错了就说错了,我的记忆力比较完整的在马列主义教研室是1978到1988我退休的时候,这中间也有一两年是在马列主义教研室,有三四年,就是1974到1978是分到数学系,数学系是跟黄见秋、李士坤他们走的。总之吧,就那几年是各自为战,没人讨论,除了讲经济学,还讲《反杜林论》,成全能的了,但是被迫的全能。
姚曼华:那时候是分到各系去了,各系管,但是这个时间还是很短,我想大概有两三年吧。基本上还是我们当时有一个党史教研室,正经有一个真正的教研室,大家在一起备课啊,讨论啊。开始的时候是一起备课讨论,后来时间长了也就不怎么一起备课讨论了,都是在家里自己备完课。有时候教研室偶然有人去听一下课,一般完全上手了,听课的就很少了,很少来检查你的课。但是教研室总是一个礼拜要开一次会吧,开会一般内容我也有点记不得了,反正跟学术上关系比较少。基本上开会的内容就是你的班是怎么搞的,你是怎么提高学生上课的兴趣的,这些方面的交流比较多。我们那个时候上课,比方说化学系,他这一年招的是200学生,就把你派到化学系讲这个课,化学系200学生我一直从头讲到底,从建党开始我一般讲到1949年吧。
请问以前上课的教材是自己编写还是有指定的?
冯瑞芳:以前都是用艾思奇的,用党校的,后来就自己编教材。哲学教研室负责编是三个人,谢龙、高宝钧和冯增铨,冯增铨已经调走了。谢龙他们是1972年才来的,原来谢龙、高宝钧、徐明都在哲学系。所以1979年开始编教材,他们三个人负责,我也参加一部分,我参加历史唯物主义那一部分,还有一些人参加。
姚曼华:也做一点研究,但我们没有很多资料,看不着很多资料。研究基本上就是研究这个人的讲稿、那个人的讲稿,像胡华的,基本上就是研究讲稿,我们讲课那时候基本上就是看别人的讲稿。
四、马列教研室的分分合合
从建国后到学院成立,马列教研室的机构设置、人员状况历经变化,请问能介绍一下基本情况吗?
冯瑞芳:我1952年到北大,那时开设了四门政治理论课,到了1964年,学校党委就决定,把这几门政治课独立出来。原来不是有两个教研室嘛,1964年7月就成立一个叫“北京大学公共政治理论课教研室”,里头分三个小的教研室,哲学、政治经济学和党史,这三门课集中起来了。当时负责人就是学校的党委副书记谢道渊,兼任大的教研室主任,钟哲明兼教研室副主任,实际工作是由钟哲明负责,他当时是宣传部的副部长,还有几个副主任,徐淑娟代表政治经济学,我代表哲学。后来到1966年春天,文革前又把我调回哲学系了。这个教研室在文革中停止了教学和科研工作,文革后就解散了。到了1972年7月,要恢复教研室了,当时还叫马列主义教研室,原北大宣传部副部长杨文娴担任直属党支部书记,萧超然是教研室主任,我跟王隽彦副主任。1974年6月,学校党委又把我们解散了,把教员分到各个系,每个系三个人。党史一个、哲学一个、经济学一个。因为我当时生病了,就没有分下去,我留在资料室给他们编点东西。马列教研室变成了“留守处”,杨文娴同志负责看守。这个又过了几年,到1977年,又恢复了,教研室主任还是萧超然,杨文娴是总支书记,我跟王隽彦是副主任。平平安安地过了几年,到了1985年又解散教研室,又回到系里头了,回到系里头我们整个教研室回去了,当时哲学系已经有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研室了,所以我们回去必须叫第二教研室,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二教研室,主任是徐明,副主任是李士坤。然后一直到了1992年成立马克思主义学院。1992年学校党委做出了《关于建立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决定》,由学校党委副书记任彦申兼院长,钟哲明为常务副院长,徐雅民、钱淦荣为副院长,赵存生为党委书记。
五、融洽的师生关系
请问那时的师生关系如何?相互之间密切吗?有些什么好的做法?
冯瑞芳:我觉得当时跟学生关系是很好的,比方说开始的时候,给学生做辅导。我当时从中央马列学院回哲学系,头一个学期就跟汪子嵩,我们深入到学生宿舍去,在学生宿舍给他们进行辅导,学生有什么就问,我们认真解答,所以跟同学关系非常好。上课不是仅仅在课堂上那点时间,还有很多课下的交流、辅导。当然那时候人比较少,一个班也就几十个人,所以都比较熟,甚至家里有什么事儿都能够交流。包括当时我们的研究生,80年代带的那些研究生,那时学生也比较少,他们家庭有什么困难,有什么问题,除了业务上沟通,其他问题也愿意跟我们讲,师生关系很好。我们那时候上课班也比较小,几十个人,全是认识的。哲学本系的,最多有四五十个人。讲公共课有时候两个系,人就多了,有的时候就一个大系。我最早讲革命史的时候,是在物理系,现在好多物理系的学生见到我们都还是比较亲切。
姚曼华:我们起码一个礼拜起码要到学生那里去三个晚上,所以能交得到朋友。我们那时候政治课教员还要做思想工作呢。就让他们信共产主义,信马克思主义,就在底下做工作。你课堂上讲的听不进去,我在底下再给你补点课。一般我们和他们年级的班主任联系很紧密的,有一个学期我就上化学系的课了,跟化学系一块儿活动,到化学系一共去了三个教员,党团活动什么的都跟他们一块儿。我们下到学生宿舍,跟他们谈一谈,提高他们的兴趣,讲一些其他方面的小的故事,比方说瞿秋白与杨之华的故事什么的,用这种办法来吸引他们。还要做一点思想工作,比方说学生之间有矛盾了,跟他们谈一谈,为人之道啊,什么都谈。作为思政课老师要做同学们的思想政治工作,组织上有这个要求。1971年从干校回来,我们都不住在家里头的,住学生宿舍。那个时候和国际政治系在一块儿,就住在国际政治系学生的宿舍,和国际政治系的学生打成一片,跟现在完全不一样,真的,你们想象都想象不出来。
作者简介:王 强 北京大学内控办公室副主任、马克思主义学院原党委副书记 讲师
赵 诺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 助理教授
前期采访:魏波、赵诺、谢超林、李茹佳、黄龙、孙振鹏、杨锐
录音整理:谢超林、李茹佳、黄龙、章天彧
后期文字整理:王强、赵诺